
撰文 | 陈缮真 意大利核物理研究院
今年4月份,杨振宁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明德讲堂”演讲时,这位97岁的物理学大咖再一次明确的反对了未来利用大对撞机进行物理研究,甚至是高能物理学的前景。
“The party is over.”
“盛宴已过。”杨先生说。
然而,杨先生口中的高能物理学的“盛宴”,是否真的已过了呢?而什么是“高能物理学”,什么又是高能物理学家们心心念念的对撞机呢?
高能物理学在研究什么?什么是对撞机?
在二十世纪之前,人类对于世界的运行规律的认知几乎都只停留在宏观物体和现象上。然而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年,从伦琴发现了X射线,J. J. 汤姆孙发现电子,卢瑟福发现了α射线和β射线等实验开始,物理学家们开始专注于微观世界的物理现象。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量子力学的建立之后,物理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在微观的尺度上,存在着一个跟宏观很不一样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的尺度如此之小,以至于物理学界们不得不借助一些特殊的实验仪器来观测其中的现象。
早期的粒子物理学研究仪器的作用通常是将微观尺度的现象放大至宏观尺度,然后再进行观测。这时期一个重要的实验仪器就是威尔逊发明的云室。云室是一种充满了过饱和蒸汽的密封空间,当微观带电粒子穿过云室时,粒子会与云室内的混合物相互作用,将其中的一些原子电离,而电离后的离子会成为云室内的过饱和蒸汽的凝结核,从而在微观带电粒子运行的轨迹周围形成雾气,进而可以被肉眼观测到。早期的粒子物理的研究目标通常都是些天然放射源以及宇宙线。1932年,安德森就是在云室中第一次发现了来自宇宙线的正电子。
笔者拍摄的位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Microcosm展览厅中的云室。云室中充满了过饱和蒸汽,并显现了数条微观粒子的运动径迹。这些微观粒子来自于土壤,岩石,水,空气等的自然辐射,以及宇宙中的宇宙线。这些径迹的粗细长短可拿来区分不同的微观粒子。
安德森观测到的正电子在云室中留下的轨迹的照片。正电子从下往上运动,在磁场中穿过一层薄薄的铅板之后,改变了轨迹弯曲的曲率。轨迹弯曲的方向表明,正电子与正常电子所带的电荷相反。(图片来自:Physical Review 43 (6): 491–494)
当年对天然放射源以及宇宙线的研究虽然可行,并且得出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通常来说这一类研究的目标都不怎么可控,粒子物理学家等到一个完美的宇宙线的事件通常要有一些运气,基本属于“靠天吃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为了更好的控制观测对象,一个更加强大的粒子物理的研究工具被发明了出来,它就是劳伦斯发明的回旋粒子加速器。回旋加速器的基本结构是两个处于磁场中的半圆D型盒,以及D型盒之间的交流电场,两个半圆D型盒上则施加有可以使带电粒子偏转的磁场。位于回旋加速器的中心处放置有一个粒子源,其发射出的带电粒子受到电场的作用被加速,在进入半圆D型盒的磁场中时,则被磁场所偏转反向,并再次进入D型盒之间的交流电场。若时间调整合适,此时交流电场的方向正好可以翻转,带电粒子则再一次被加速。如此往复很多次,带电粒子就会被加速至带有较高的能量。
劳伦斯在1930年左右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制作的第一个回旋粒子加速器。(图片来自: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劳伦斯发明的回旋粒子加速器的工作原理(图片来自: U.S. Patent 1,948,384,Ernest O. Lawrence --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the acceleration of ions (1934))
回旋粒子加速器使得人类能够可控的获得了带有较高能量的微观带电粒子,进而可以更准确的研究这些粒子的性质。然而由于相对论效应,高能量的粒子的回旋周期会随能量的增高而发生改变。于是科学家们将回旋粒子加速器的均匀磁场以及电场变化频率也做了调整,使之能够最大程度的使带电粒子获得能量。这种电场及磁场可控的粒子加速器叫做同步加速器。同时改变电场和磁场,也使得带电粒子在加速的时候不必须经历一个变化的半径,因此,同步加速器可以被做成环形。
环形加速器的结构可以持续地将粒子加速,粒子会重复经过环形轨道上的同一点。但是这一种加速器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在很高的能量的情况下,粒子的能量会以一种叫做同步辐射方式被发散出去,并达到一个极限。想要继续提高能量,就只能增强磁场并增大环的周长。然而这种对于粒子物理学来说是浪费能量的同步辐射并非一无是处,它会以一种高能量,高纯净度,高准直的电磁波的形式被发散出去,而这种电磁波则可以用作衍射分析,也早已被广泛的应用在了材料学、结构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中。
笔者拍摄于CERN的同步回旋加速器。建成于1957年的它曾是CERN的第一个加速器,能够将粒子加速到600兆电子伏特的能量。现在早已退役的它被安置于一个颇具蒸汽朋克感的展厅中,与众多半个世纪前的研究用仪器和物品一起展示着CERN的历史。
另一种加速带电粒子的方式是利用直线加速器,直线加速器不存在同步辐射的问题,但是粒子不能被重复加速,相同时间内能够被加速的粒子数通常会远小于环形加速器,并且通常加速器需要被做的很长。虽然直线加速器这个名词看起来可能会有些陌生,但是其实这种脱胎于粒子物理研究的仪器早就走进过人们的生活。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很多都接触过直线加速器,那就是以前电视机和计算机显示器中的阴极射线管。阴极射线管显示器就是利用阴极电子枪发射电子,在阳极高压的作用下进行加速并射向屏幕,同时电子束在偏转磁场的作用下,快速的进行上下左右的移动并扫描整个屏幕。屏幕中的荧光粉在电子的作用下发光,进而达到显示图像的目的。
彩色阴极射线管的剖面图: 1. 电子枪2. 电子束 3. 聚焦线圈 4. 偏向线圈 5. 阳极接点 6. 电子束遮罩区隔颜色区域 7. 荧光幕分别有红绿蓝萤光剂分区涂布 8. 彩色萤光幕内侧的放大图(图片来自:维基百科:阴极射线管)
由于相对论效应,想要研究更精细的结构,就必须获得更高的能量。有了加速器这样一个研究利器,粒子物理学家们就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可控的高能量,于是粒子物理学的主要研究方式就变成了利用高能粒子加速器进行研究。因此,粒子物理学现在也被称为高能物理学。
早期的加速器主要用来加速的带电粒子并轰击原子靶,进而对轰击产物进行统计分析。丁肇中在发现1974年发现J粒子(后来被称为J/ψ粒子)的实验就是利用加速的质子束轰击铍靶,并分析其产物的分布而完成的。随着粒子物理实验的进展,粒子物理的理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一些能量更高的粒子被预言,而想要产生这些粒子,需要建设更高能量的实验设备。并且,利用被加速的粒子束来轰击固定靶的实验形式将绝大多数的能量浪费在了轰击产物的动能上,于是,实验物理学家们开发了另一种节约能量的办法:加速两束相反方向的粒子,让他们在极小的空间内对撞。而这,就是目前粒子物理学研究的终极武器,对撞机。
个人英雄主义的盛宴?合作精神的盛宴?
历史讲起来总比当年的探索容易。对撞机的发展逐渐远远超出的几个人单打独斗就能解决的范畴。想要让两束微观粒子对撞,则必须让接近光速运动的粒子束流控制在纳米级的精度之内。而这,则需要极高精度的控制管理系统,极高强度,极高精度的磁场,以及高极效率,极高精度的探测系统。而这一套系统的搭建,则需要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由于实验获得的数据的统计量也呈几何级数般增长,这些数据也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做多元化的分析。实验高能物理学大型国际合作组的雏形就在那个年代出现。
ATLAS实验(CERN的一个粒子物理实验)国际合作组的成员的国籍分布。ATLAS实验有着来自103个国家的5500多名科研人员,世界上的大多数的国家都有科研人员为这一个国际合作实验做贡献。(图片来自:CERN)
杨振宁在物理学界活跃的年代在半个多世纪前。也就是那个年代的物理学家们亲手栽下了粒子物理学这一棵树苗。在那个粒子物理学起步的年代,确实涌现出了很多先驱和孤胆英雄,他们带来了创新,带来了发展,为粒子物理学这一棵树苗带来了甘霖雨露。当年的粒子物理学理论正在成立之初,在茫茫未知领域凭借个人能力常常就能领略到惊鸿一瞥。当年的粒子物理学实验也通常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完成。比如吴健雄女士证实李政道与杨振宁宇称不守恒猜想的实验的文章只有五位作者,丁肇中发现J粒子的文章也只有14位作者。
而如今的粒子物理学已经发展成一株参天大树,一株个人英雄主义已无法撼动的大树。信息互联使得大型合作成为可能,研究进展的速度也今非昔比。凭借团队合作,一些半个世纪前被视为难以企及的理论的验证逐渐变得能轻松实现, 而一些半个世纪前难以想象的实验仪器也逐渐成为现实。1964年,为解决基本粒子质量起源的问题,数位物理学家提出了叫做希格斯机制的猜想。这个猜想固然惊艳,然而,得不到实验验证的猜想终究只能是猜想。二十一世纪,为了验证包括希格斯机制在内的几十上百个理论,实验粒子物理学家就建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实验仪器,周长达到27公里,极具科幻感的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以及相应的探测器,并在其正式投入运行后的第二年(2012年)证实了希格斯粒子的存在,为当时仍然在世的希格斯机制的提出者弗朗索瓦·恩格勒和彼得·希格斯带来了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安装中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的四个主要的探测器。它们分别是ATLAS(左上),ALICE(右上),CMS(左下),LHCb(右下)。(图片来自:CERN)
然而希格斯粒子的发现,就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的终结吗?远远不是的。希格斯机制是被证实了,然而超对称,暗物质,电荷—宇称不守恒等等问题依然还未被解决,LHC在发现了希格斯粒子之后仍然有二十多年的运行计划,并会经历数次升级。这期间科学家们将在LHC继续他们的探索。
一个学科的萌芽状态往往是孤胆英雄大显神通的时候,然而当这个学科发展到系统化规范化的时候,往往就需要更有力的团队协作。现在大飞机的设计不再能只靠莱特兄弟,计算机技术的创新也早已难以仅靠两三人从车库中萌芽,而航天科技,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宏大的项目,也都需要千万人的共同协作。在这个年代,个人英雄已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合作使得很多科研探索实验成为了英雄集结的“聚义厅”。 从这种意义来说个人英雄主义的“盛宴”确实已过。然而,对于全球范围的科学合作来说,觞宴却在正酣时!
未来应何去何从?
那么,LHC之后的高能物理学将何去何从呢?由于目前的LHC的局限性,即便是希格斯粒子,对高能物理学家们来说,也仍有着太多的未知等待着被揭示。为了更细致的研究希格斯粒子以及其他一些物理理论,各国粒子物理学家们都提出了建设下一代对撞机的构想。这其中就包括中国提出的CEPC计划,日本想要承接的ILC计划,以及欧洲的FCC-ee计划。这些计划虽然各有千秋,但是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为希格斯粒子的产生进行的参数优化,都可以精细的研究希格斯粒子的各种性质,它们都可以被称为“希格斯工厂”。
然而,为何在发现了希格斯粒子之后,仍然要对它进行研究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类比一下人类对冥王星的探索历程。
1994年和2018年人类所认知的冥王星的对比图。左图来自哈勃空间望远镜,右图来自新视野号航天器。(图片来自:NASA)
上面是1994年和2018年人类所认知的冥王星的对比图。1994年,人类通过哈勃空间望远镜拍摄到的冥王星已达到了地球上人类对其认知的最高的分辨率,而2018年视野号航天器飞临冥王星,则为人类第一次带来了它的高清图。
冥王星可是1930年就已经被人类发现了啊,当时几个像素的图像也能表明它是一个围绕太阳运动的行星,为什么人类还要继续对它探索呢?为什么到了21世纪,人类还要发射新视野号这样的航天器,并花十几年的时间,把它送去冥王星的附近呢?
因为我们不了解冥王星,因为我们想去了解它。
现在我们已知道了冥王星的质量,轨道倾角,离心率,拍了高分辨率的照片,甚至了解了它的成分组成,但是人类的求知欲是不会被填满的。新视野号探测器这两年发现,冥王星地底下可能有由半融化水冰而成的海洋,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冥王星地底可能有热源存在。这不是宣布了对冥王星研究的结束,而是给下一步对冥王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开启了更多的研究可能。
对于希格斯粒子的研究,也是类似的。
现在人类所认知的希格斯粒子,就像是1994年人类所认知的冥王星,只有上百个像素。而这上百个像素,已经足以指明一个未来研究进展的方向,而CEPC,ILC,FCC-ee,它们就是希格斯粒子的“新视野号”。它们迟早也会给人类画出一张高清的希格斯粒子的图像。
那么,对于希格斯粒子的研究,能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什么呢?
答案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粒子物理的研究是数辈人从上上个世纪末开始到现在一脉相承的。1897年发现电子,1919年发现质子,1932年发现中子和正电子,1937年发现μ子,1947年发现π和K介子,1956年发现电中微子,1974年发现J/ψ粒子,1975年发现τ子,1983年发现W、Z玻色子,1995年发现顶夸克,2012年发现Higgs玻色子,未来则一定还会发现新的东西。而1897年发现电子的时候,人们肯定也想不到如今的生活已经离开不了那么多的电子器件(甚至都已经淘汰了很多,比如电视机的阴极射线显像管)。1932年发现正电子的时候,当时的人肯定也想不到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技术(PET-CT)可以在无创伤的情况下对人体进行早期肿瘤筛查,从而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1919年发现质子和1947年发现π介子的时候,人们依然无法预料到它们在半个世纪之后治疗癌症的辐射疗法中的应用潜力。
粒子物理学的研究是超前于时代的,谁也不能保证,若干年后,这些看似高冷的研究成果会有怎样的颠覆人类生活的应用。而对撞机则目前粒子物理研究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即使在中国对于是否应该建设下一代大型对撞机有着广泛争论的今天,即使是经费没有到位的今天,实验粒子物理学家们仍然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下一代对撞机的预研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这承载着人类对于这个宇宙运行规律的认知的未来。
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或许杨先生曾是离当年星空最近的人,但是,前赴后继的科研后辈们依然有仰望今时星空的权利,更何况,如今的星空比当年更璀璨。

 全国人大代表刘宏志: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激发乡村振兴“数智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刘宏志: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激发乡村振兴“数智力量” 瑞能半导体再次荣获海尔卡奥斯创智物联战略供应商奖
瑞能半导体再次荣获海尔卡奥斯创智物联战略供应商奖 张雪峰成为国货鼠标品牌英菲克代言人
张雪峰成为国货鼠标品牌英菲克代言人 二十城联动,一加 Ace 3 Pop-up 快闪活动火爆开启
二十城联动,一加 Ace 3 Pop-up 快闪活动火爆开启 “低调实力派”盘点虬龙科技在电动越野领域走过的十年
“低调实力派”盘点虬龙科技在电动越野领域走过的十年 瑞能半导体出席北京证券交易所国际投资者推介会
瑞能半导体出席北京证券交易所国际投资者推介会 大有时空精彩亮相第一届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大会,尽显强劲实力
大有时空精彩亮相第一届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大会,尽显强劲实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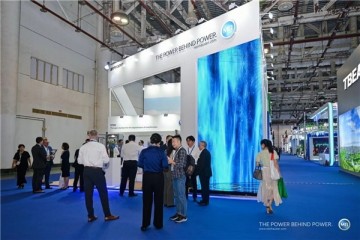 MR出席CEPSI 2023探索行业未来,卓越方案诠释“绿色明天”
MR出席CEPSI 2023探索行业未来,卓越方案诠释“绿色明天”